|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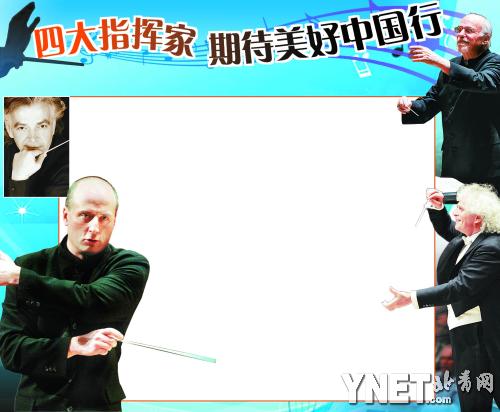
西蒙-拉特、帕沃-雅爾維、克勞斯-彼得-弗洛爾、大衛(wèi)-津曼
國家大劇院的11月將是名家薈萃的一個(gè)月。其中,在國家大劇院的音樂廳,四個(gè)世界著名交響樂團(tuán)的到來將點(diǎn)燃樂迷們的熱情。柏林愛樂樂團(tuán)、法國巴黎管弦樂團(tuán)、瑞士蘇黎世市政廳管弦樂團(tuán)和捷克愛樂樂團(tuán),每一個(gè)都是響當(dāng)當(dāng)?shù)模麄儗硭姆N不同的音樂風(fēng)格。而執(zhí)棒四大樂團(tuán)的指揮家西蒙·拉特、帕沃·雅爾維、大衛(wèi)·津曼和克勞斯·彼得·弗洛爾也都在國際上赫赫有名。他們并非第一次來中國,但每一位都對(duì)新的一次中國之行有著美好的期待。
西蒙·拉特:
做柏林愛樂的指揮是一個(gè)挑戰(zhàn)
六年前的北京國際音樂節(jié)上,西蒙·拉特帶領(lǐng)柏林愛樂樂團(tuán)來到北京,使得北京樂迷在經(jīng)過了整整一個(gè)阿巴多時(shí)代后再次聆聽到柏林愛樂樂團(tuán)的現(xiàn)場演奏。這次在國家大劇院的演出,距上次時(shí)間并沒有那么久,但樂迷的熱情依舊,演出票早早就銷售一空。這一次柏林愛樂樂團(tuán)帶來的是馬勒第九交響曲和布魯克納第九交響曲,以及日本作曲家細(xì)川俊夫的《那時(shí)花開》。西蒙·拉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shí)說:“擔(dān)任柏林愛樂的指揮是指揮們的夢(mèng)想,因?yàn)槭澜缟蠜]有其他樂團(tuán)能夠與之匹敵。我指揮過很多非常棒的樂團(tuán),但沒有一個(gè)團(tuán)擁有這樣的實(shí)力。這也是一個(gè)很年輕的樂團(tuán),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家們交匯融合,做他們的指揮是一項(xiàng)很大的挑戰(zhàn)。”
近年來柏林愛樂樂團(tuán)演奏馬勒作品并不多,西蒙·拉特告訴記者:“馬勒那個(gè)時(shí)代,很多指揮家本身就是作曲家。我對(duì)馬勒的感情是很個(gè)人的,作為一個(gè)指揮家,我總是將他看成中歐音樂的領(lǐng)導(dǎo)者,他有一股火焰般的力量。我到柏林愛樂后,故意避免上演馬勒作品,因?yàn)樵诎投嘀笓]下,樂團(tuán)演奏了很多馬勒作品,我認(rèn)為他們要從那種風(fēng)格中走出來。現(xiàn)在,我們又回去了,我必須要讓樂手們有種度假歸來的新鮮感,這樣才能重新創(chuàng)造,重新發(fā)掘,才能投入。”
對(duì)于北京的觀眾,西蒙·拉特領(lǐng)教了他們的專業(yè)精神,他說:“作為世界的一部分,我和柏林愛樂都覺得中國是音樂世界的未來,大家都很振奮。我們也發(fā)覺中國有很多專業(yè)的聽眾,他們既有幽默感也很專業(yè),當(dāng)我們演奏出美妙音樂的時(shí)候,大家也都有熱烈的反應(yīng)。沒錯(cuò),我上次帶團(tuán)訪問北京、上海、香港和臺(tái)北,就感受到年輕人對(duì)古典音樂濃厚的興趣。”
大衛(wèi)·津曼:
馬勒是一個(gè)預(yù)言家
著名指揮家大衛(wèi)·津曼帶來的瑞士蘇黎世市政廳管弦樂團(tuán)11月5日將為北京觀眾演奏馬勒第五交響曲,這一次的馬勒與上一次新年音樂會(huì)是不同的作品。大衛(wèi)·津曼對(duì)記者說:“我覺得,馬勒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預(yù)言家。他的音樂預(yù)示了現(xiàn)代音樂。不是說他的音樂很現(xiàn)代,而是說他使用的作曲技法,其音樂表現(xiàn)出來的人性是非常現(xiàn)代的,更接近于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站在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要比馬勒的同代人更容易理解馬勒。他的音樂在預(yù)言未來的人性,正如貝多芬在音樂中表現(xiàn)出來的那樣。”
大衛(wèi)·津曼是一位馬勒專家,他已經(jīng)錄制了兩套馬勒全套交響曲的唱片,他對(duì)記者說“我們通過馬勒的成長背景、他的國家、他所受的教育、他最初的音樂偶像等等這些來理解馬勒。馬勒音樂的風(fēng)格前后改變非常大,他越來越執(zhí)著于用自己的方式表達(dá)音樂。看馬勒,我的切入點(diǎn)是他的聲樂套曲。先通過聲樂套曲了解馬勒。尤其是《少年的魔角》,這是理解馬勒第四交響曲的關(guān)鍵。理解馬勒,先是他的套曲,然后才是交響樂及其他的音樂形式。”
說到他本人最喜歡的馬勒作品,他說:“我曾說過第四交響曲在某種程度上堪稱完美,但是馬勒的每一首交響曲對(duì)他來說都是新的開始。任何一首作品都是不可替代的,彼此風(fēng)格迥異,他們都是全新的音樂嘗試。我的確非常喜歡第四交響曲,但實(shí)際上他的每首交響曲我都喜歡。如果可能的話,我愿意演出他的全部曲目。”
克勞斯·彼得·弗洛爾:
馬勒的音樂寫給所有人
著名作曲家馬勒在捷克出生,因此,捷克愛樂樂團(tuán)被認(rèn)為是來自馬勒出生地的樂團(tuán),而指揮家克勞斯·彼得·弗洛爾說:“我認(rèn)為,任何一支喜愛馬勒的樂團(tuán)都有能力把他的作品演好,這與作曲家的出生地沒有關(guān)系。并不是因?yàn)轳R勒的家鄉(xiāng)就在附近,捷克愛樂樂團(tuán)才致力于演奏馬勒。就像我不認(rèn)為倫敦的樂團(tuán)善于演奏亨德爾,因?yàn)楹嗟聽栐谟钸^。我認(rèn)為捷克愛樂樂團(tuán)取得的成績與全世界古典音樂的發(fā)展有關(guān)。斯美塔那、德沃夏克等大師的耕耘,德語區(qū)樂團(tuán)對(duì)演奏晚期浪漫派作品的熱情,以及這支樂團(tuán)本身的實(shí)力,共同打造了它演奏馬勒作品的實(shí)力。”
對(duì)于捷克愛樂樂團(tuán)演奏的馬勒第六交響曲,弗洛爾說:“我就馬勒第六交響曲已經(jīng)寫作了多部專著,恐怕這個(gè)問題沒有簡短的回答。我盡量一言以蔽之,馬勒盡管孤獨(dú)一人,他的音樂卻是寫給所有人,是面對(duì)面地從每位聆聽者身上獲得憐憫。這部作品是他描寫自己作為人類與命運(yùn)的抗?fàn)帯_@是他個(gè)人的悲劇,也是這部交響曲所描寫的悲劇。我今年已經(jīng)在上海和廣州指揮了馬勒的第五和第六交響曲。這并非是我個(gè)人的選擇,而是我與樂團(tuán)共同商議的結(jié)果。”
捷克愛樂樂團(tuán)還將演奏德沃夏克第九交響曲“自新大陸”,弗洛爾說:“我想每個(gè)人聽到這部作品時(shí),都會(huì)對(duì)其中美輪美奐的和聲及旋律產(chǎn)生個(gè)人化的理解。我其實(shí)不必對(duì)“自新大陸”描述太多,因?yàn)椤白髑乙呀?jīng)都寫在作品里了。”
帕沃·雅爾維:
展現(xiàn)巴黎管弦樂團(tuán)的獨(dú)特傳統(tǒng)
巴黎管弦樂團(tuán)這一次來到北京將帶來的作品是他們最拿手的,指揮家帕沃·雅爾維說:“巴黎管弦樂團(tuán)本來就十分擅長于演奏浪漫主義時(shí)期的作品以及現(xiàn)代作品。這一次到北京,我們帶來的也是非常具有巴黎管弦樂團(tuán)特色的拿手曲目,包括梅西安的《被遺忘的祭品》,和鋼琴家大衛(wèi)·弗雷合作拉威爾的《G大調(diào)鋼琴協(xié)奏曲》,還有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魯什卡》。這三首曲目完全體現(xiàn)了樂團(tuán)在新的演出季中的思考。”
對(duì)于這三首作品,帕沃·雅爾維說:“法國人的浪漫大概是舉世聞名的,法國作曲家的作品也充滿了這樣的特質(zhì),二十世紀(jì)的法國音樂相當(dāng)耀眼。梅西安是非常偉大的法國現(xiàn)代作曲家,《被遺忘的祭品》是梅西安22歲從巴黎音樂學(xué)院剛剛畢業(yè)時(shí)完成的作品。而拉威爾自然是具有濃郁法國風(fēng)情的印象派作曲家,《G大調(diào)鋼琴協(xié)奏曲》是他1933年的作品,同時(shí),我很高興能將鋼琴家大衛(wèi)·弗雷介紹給中國觀眾,我聽說這是他首次來中國演出,他非常棒。我想,法國音樂是巴黎管弦樂團(tuán)的根本和特色。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魯什卡》這部作品,當(dāng)時(shí)由尼金斯基首演,也成為尼金斯基的經(jīng)典形象。我也力求用音樂來完成這個(gè)經(jīng)典的木偶形象,相信這會(huì)非常有趣。”
帕沃·雅爾維說:“2008年北京奧運(yùn)會(huì)前夕,我曾跟法蘭克福廣播交響樂團(tuán)一起到中國演出,其中有一站就是當(dāng)時(shí)剛啟用的國家大劇院,演出的曲目全是瓦格納和勃拉姆斯的作品,那場演出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但我想,德奧作品和法國作品的風(fēng)格是截然不同的,我想看看這一次國家大劇院的觀眾會(huì)給我怎樣的反饋。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很期待我的到來,但是我已經(jīng)很期待演出給他們聽了。我的家族和中國有著很深的淵源,我的父親和弟弟都曾先后來北京演出過,尤其是我的父親他對(duì)北京的印象極好,他們回去之后都有跟我談起來中國的感受以及他們演出的情況。我也想更多的去感受中國這個(gè)古老的國度,去感受中國的觀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