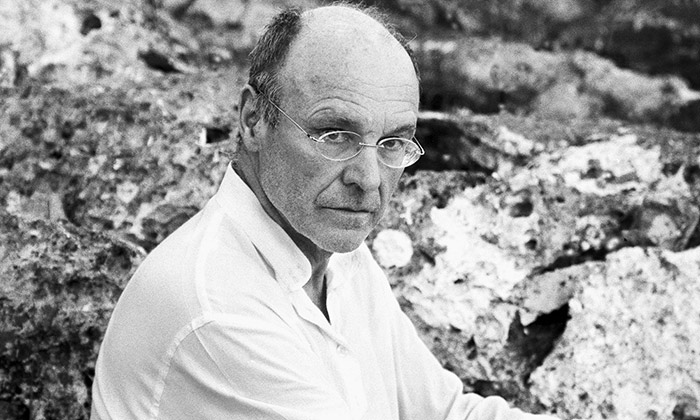
安塞爾姆·基弗 ? ANSELM KIEFER/PHOTO: RENATE GRAF
文/段琳
安塞爾姆·基弗是戰(zhàn)后德國最重要的新表現(xiàn)主義藝術(shù)家之一,八十年代末的基弗作品采用了德國身份的主題和符號,對當(dāng)時被冷戰(zhàn)分裂的東西德的歷史文化與記憶作出了清晰的表達(dá)和對自我身份構(gòu)建的理解。基弗在冷戰(zhàn)結(jié)束、柏林墻被推倒的前一年移居法國,完成了跨國界跨文化的藝術(shù)轉(zhuǎn)型,并對多元化時代背景下藝術(shù)家如何進(jìn)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如何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完善自我發(fā)出疑問。
在基弗諸多繪畫作品中,“地平線”是不可忽略的畫面元素,人們通常把“地平線”理解為未來,而基弗的風(fēng)景畫除了這種理解之外還將其描繪成時間和集體意義對人類的展露。這清晰的地平線象征著基弗對歷史與未來的清晰判斷,這是一條結(jié)合歷史與未來的線,也是一條貫穿基弗對自我身份定義的線索。

基弗在創(chuàng)作中 ? ANSELM KIEFER
對身份的定義是貫穿基弗藝術(shù)作品的線索,不僅是淺顯的指向東德或是西德,是國家社會主義或是民族根性文化,還是“德國性”與“國際化”的區(qū)分或融合。對身份的追尋和界定,更深層次的還是集中到藝術(shù)家自我的認(rèn)知和探尋,這不止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和完善,更是藝術(shù)家整體人格的提升。
在基弗任何時期的藝術(shù)作品中,我們都可以觀察到他對“過去”的反思和“當(dāng)下”的思考,無論是六十年代中后期他對重要藝術(shù)思潮和學(xué)潮運(yùn)動的回應(yīng),還是八十年代初作為新表現(xiàn)主義者領(lǐng)袖領(lǐng)導(dǎo)的藝術(shù)界的國際運(yùn)動,基弗都是以在場的身份參與其中,并在思考東西德歷史、記憶和身份認(rèn)同的爭論之后通過藝術(shù)作品傳達(dá)出自己的立場和態(tài)度。

基弗在創(chuàng)作中 ? ANSELM KIEFER
德國是“二戰(zhàn)”戰(zhàn)敗國并被冷戰(zhàn)分割為兩種意識形態(tài)不相容的兩個國家,在國家的意志和個人意志的矛盾,被外界所定義的意識形態(tài)和民族文化根性的矛盾,服從集體跟隨社會主流和服從個人意志的矛盾等關(guān)系下膠著生活的德國本土人民,“何去何從”是年輕人必為思考的問題,在這樣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基弗,自然會提出疑問并作出選擇,他的藝術(shù)作品也必然包含了這些問題。藝術(shù)家的發(fā)聲是個人對社會和集體拋出的疑問。

《鐵軌》,1986年,油彩、丙烯和乳劑于畫布,帶有橄欖枝、鐵和鉛,220×380cm
《鐵軌》是基弗帶有強(qiáng)烈批判色彩的典型“二戰(zhàn)”歷史題材作品,是在哀悼一場屠殺,也是對納粹的指責(zé)和自我反省。畫面中的地平線位于畫面上方的八分之一處,廣闊荒蕪的大地上遍是塵埃,即便畫面上只留有在地平線處交匯分叉的鐵軌而無主體人物,也會讓觀眾體會到曾經(jīng)在這片土地上發(fā)生過的“哀鴻遍野”,但也許無聲的寂靜更加具有恐怖的力量。地平線仿佛懸掛在盡頭,對于乘上列車駛在鐵軌上的人來說,盡頭又是什么呢,絕望與哀傷之處,地平線仿佛是死亡,也仿佛是另一種希望。鐵軌作為工業(yè)革命的產(chǎn)物,是人類與科技文明高速發(fā)展的產(chǎn)物,是戰(zhàn)爭中便利人民逃生的工具也是成為屠殺的幫兇,這是值得人類在戰(zhàn)后反思的問題,也是勇于回顧民族歷史錯誤的基弗以此為題作畫的目的之一。這幅作品在材料的選擇上使用了象征和平的橄欖枝,被橄欖枝勾畫的鞋履似是終要從戰(zhàn)爭解放出來,一步步邁向通往和平的未來,歷史與未來被基弗畫面上的地平線分隔開,但同樣也交融在一起。

《為韋利米·赫列勃尼科夫而作:戰(zhàn)爭理論——海戰(zhàn)》 2004年—2010年 油彩、乳劑、蟲膠、麥秸和鉛于畫布 190×330cm
海岸線是大海與天空的“地平線”。《為韋利米·赫列勃尼科夫而作:戰(zhàn)爭理論——海戰(zhàn)》是基弗創(chuàng)作于2004年的《為韋利米.赫列勃尼科夫而作》三十幅組畫中的其中一張,在這張作品里基弗把海平線放置在畫面極高出,畫面上的麥秸和乳膠盤根錯節(jié)的突顯了海洋波瀾寬廣、波濤洶涌的氣勢,一艘軍艦似海怪般盤踞在海面上,風(fēng)雨欲來,仿佛海洋會化成血域的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人類因?yàn)樨潙賹ψ匀坏钠茐模瑢ι`的涂炭,使基弗在這張作品里對戰(zhàn)爭帶來的危害作出了指責(zé)和反思,但他卻用暴力美學(xué)使戰(zhàn)爭美化,這不是對歷史的緬懷而是紀(jì)念碑式的崇高美哀悼戰(zhàn)爭,哀悼曾經(jīng)丟失的和平以及對后人的警示,還有作為德意志民族在“二戰(zhàn)”后的靈魂救贖。

《隕落的星星》1995年 畫布油畫 230×170cm
作品《隕落的星星》中的地平線位于畫面下四分之一處,基弗用幽冷的藍(lán)色線條將作品劃出天空與大地的界線也仿佛是生與死的界線,地平線之上是占用畫布面積四分之三的黑夜,巨大的黑色幕布上滿是即將隕落的星星,這黑夜仿佛同樣暗示了人類未知的死亡與虛無。這是基弗平躺于大地的臥姿自畫像,半僵硬的平靜姿態(tài)似乎預(yù)示著躺在地上的人已經(jīng)做好了星星即將隕落在自己身體上的準(zhǔn)備,死亡和孕育一直是神秘的話題,這種神秘化是基弗作為異鄉(xiāng)人的特質(zhì)之一,而《隕落的星星》也的確是五十歲的基弗在法國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這種回歸生命本質(zhì)的話題,與中國常說的“五十而知天命”不謀而合,而天命本是神秘化不能闡釋極盡而人類卻傾其所有不斷追尋的。對天命的追問,也是人類對追尋自我的方式之一,人究竟何以為人,人何以來世,人何以作為,人何以離世。

《躺在海邊的波西米亞人》,1995年,油彩、乳劑、蟲膠、炭筆和粉末涂料于粗麻布, 190×559cm
《躺在海邊的波西米亞人》是基弗創(chuàng)作的一張法國風(fēng)景畫,在畫面中極高的地平線上用德文寫有奧地利詩人巴赫曼的詩歌標(biāo)題。波西米亞主義提倡精神上的絕對自由,自我流浪和追逐,這像極了巴赫曼的一生,巴赫曼曾先后和猶太詩人策蘭、音樂家恒茨相愛卻未得善果,最后與瑞士作家弗里希的愛情也因?yàn)樾愿癫町惗珠_,這個在情感上未得愛神眷顧、在戰(zhàn)火中飽受流離卻在文學(xué)詩歌上造詣極高的女詩人終期一生的尋找在基弗作品里的化為了一種平靜,這也許是基弗對巴赫曼詩歌的解讀。《躺在海邊的波西米亞人》與《鐵軌》的構(gòu)圖極為相似,但不同的是橫貫在畫面上的地平線和小徑上綴滿了粉色的花朵,優(yōu)美而浪漫的鋪開在觀者面前,仿佛預(yù)示著這位生活跌宕的巴赫曼將重新和世界結(jié)締聯(lián)系。基弗構(gòu)建了一個波西米亞人在海邊對平靜之地的幻想,而這正是巴赫曼所渴求卻深知她永遠(yuǎn)無法體驗(yàn)到的境界。

基弗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
基弗作品的可闡釋性是他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特質(zhì)之一,但這種多元化闡釋也會導(dǎo)致對畫面的無解讀性,兩者雖然矛盾,但這正是基弗作品的魅力。矛盾從另一層面看意味著作品的包容性,也意味著基弗的中立和邊緣性。藝術(shù)家把更多的閱讀和感受投向觀眾,帶動觀眾思考,增強(qiáng)與觀眾的互動,而不是一味的將自己的思想植入給他人,這種始終帶著批判意味、辯證觀看事物的角度,使基弗從個人跨越到集體,從德國性視角跨越到國際性視角得到完美轉(zhuǎn)型,這樣的包容性奠定了他國際性頂級當(dāng)代藝術(shù)家的地位。

觀眾觀看基弗的作品
在基弗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藝術(shù)已非對物體的純粹描繪,而是經(jīng)過不斷提煉的、系統(tǒng)性的、有序的排列,他把歷史、文化、記憶、宗教、詩歌等元素相互糅雜然后帶入到自己的知識體系之中,再用更廣闊的視野將其重新解釋,而作為觀眾所得到的并不僅是視覺上的沖擊力和創(chuàng)新,基弗的作品更像是思想的復(fù)合體,不受時代的局限性,成為帶有基弗極強(qiáng)個人哲學(xué)特點(diǎn)的經(jīng)典。

基弗的工作室 ? ANSELM KIEFER
銜接歷史與未來的地平線,是本文分析基弗藝術(shù)創(chuàng)作歷程和分析其藝術(shù)作品的切入點(diǎn)。時間劃過歷史,讓過去的故事遺留給今天去解讀,但同樣也是歷史豐富了時間的內(nèi)涵,往事雖不可追,但可以為后人留鑒,不可知的未來也會是無數(shù)個現(xiàn)在堆積起來的。用基弗自己的話說,廢墟總是一種新的建造的開始,它本身就是未來。

基弗在工作室 ? ANSELM KIEF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