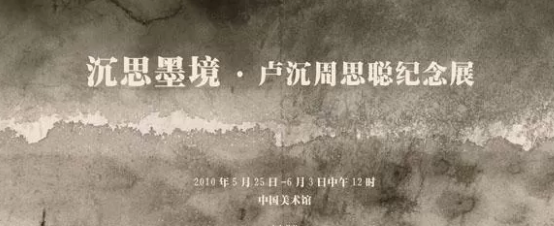20世紀,對于中華民族,是苦難深重,同時又在艱難之中孕育著復興的百年。1917年,胡適和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fā)起文學改良運動;孫中山北上征討軍閥,保護革命果實;留法勤工儉學會成立,中國第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即將赴歐洲求學……黑暗的舊中國仍然混沌未開,然而新的思潮已在涌動萌發(fā)。
這一年的農(nóng)歷五月十九日,張仃出生于遼寧北鎮(zhèn)醫(yī)巫閭山下周屯,他本名冠成,字豁然。在這個被他戲稱“只產(chǎn)白薯和胡子”的地方,每年四月,家鄉(xiāng)的廟會是張仃最開心的時候,而廟里的壁畫成為張仃幼年藝術(shù)最初的啟蒙。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東三省淪陷。年僅14歲的張仃輟學,流亡至北平。因喜歡藝術(shù),他不顧家人反對,考入北華私立美術(shù)專科學校的中國畫系。他同情(目睹)底層人民的悲慘生活,對(國民黨)不抵抗行為極為憤慨。他逐漸發(fā)現(xiàn)了漫畫這一主題鮮明、風格犀利的藝術(shù)形式,并把它為匕首投槍,向社會黑暗宣戰(zhàn)。因參與積極進步活動,1934年張仃被國民黨憲兵逮捕,押送至南京。張仃的漫畫想象力天馬行空,筆下的作品簡練、準確、有力,對感情的表達直接、有力,極富煽動性。年輕的張仃,因為漫畫,像一聲霹靂,響徹中國文藝界(走上了革命之路)。
1938年秋,張仃來到延安。延安的物質(zhì)條件雖然艱苦,卻充滿了理想和革命精神。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普天同慶。在這期間,張仃承擔了為國家而設(shè)計的光榮使命。他負責改造勤政殿與懷仁堂,為全國政協(xié)設(shè)計會徽與紀念郵票,為開國大典進行美術(shù)設(shè)計,并負責天安門的裝修方案。在國徽設(shè)計中,張仃提出國徽中必須要有天安門,這一意見最終被采納,成為國徽中最重要的標志,這一系列重大的設(shè)計任務(wù),使得張仃被后人稱為“新中國的首席形象設(shè)計師”。
年輕的新中國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形象,1951-1956年間,張仃將中國國家館帶往布拉格、莫斯科、巴黎、華沙、萊比錫、羅馬等城市的博覽會,這一時期,張仃確定了民族加現(xiàn)代的國家風格形象,讓國外觀眾眼前一亮,(把朝氣蓬勃的新中國形象帶給了世界)充滿朝氣的中國氣派給世界留下了鮮明的印象。
1956年,因為在巴黎主持世界博覽會的中國館設(shè)計工作,張仃有機會見到了畢加索。
1950年,中央美術(shù)學院成立,張仃擔任實用美術(shù)系主任。當時中國畫的發(fā)展面臨困境,對于中國畫的前途,一派認為中國畫已經(jīng)高度成熟,無需變革,另一派則認為中國畫是封建時代的產(chǎn)物,無法表現(xiàn)新時代。當時張仃與李可染都住在大雅寶胡同,每天早晨他們都相約一起去上班,一路走,一路聊,探討著關(guān)于中國畫發(fā)展的問題。1954年,美術(shù)界再起中國畫問題的爭論。中央美術(shù)學院成立國畫革新小組,由張仃任組長。由此,張仃、李可染、羅銘進行了著名的江南水墨寫生,他們希望通過一次具體的藝術(shù)實踐,為古老的中國畫探索出一個新的未來。1956年,國務(wù)院組織(毛澤東、周恩來批示)成立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院,但緊接而來的“反右”運動,讓學院的一批藝術(shù)家和學者紛紛落難。1957年,黨中央派張仃擔任副院長,他一方面把民間藝術(shù)請入學校,同時又吸收西方現(xiàn)代設(shè)計藝術(shù)精華。
1961年,張仃帶研究生云南寫生,創(chuàng)作出了一批讓人大開眼界的“裝飾繪畫”。這是人們從未見過的中國畫新樣式。但正是這批帶有這些新觀念、新探索的作品,為張仃帶來了不盡的災難。而這時,一本掖在口袋里的巴掌大的黃賓虹的焦墨冊頁成為他藝術(shù)上的唯一慰藉。在荒山野嶺之中,沒有任何可以作畫的工具,他只得向小學生借來最簡單的筆、紙、墨,在一筆一畫之中,他找到了巨大的安靜,也開啟了他晚年向藝術(shù)高峰的跋涉。
改革開放之后,百廢待興。61歲的張仃眾望所歸,復任中央工藝美院副院長。當年,他為上海美術(shù)電影制片廠設(shè)計了動畫片《哪吒鬧海》,并在1979年從全國藝術(shù)院校調(diào)兵遣將,主持了首都機場壁畫的創(chuàng)作。張仃用篆書的“藝”字設(shè)計的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院校徽一直用到今天,他確立的“衣”、“食”、“住”、“行”至今仍是中國設(shè)計發(fā)展的重要方向。在張仃的帶領(lǐng)下,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院毫無疑問成為“中國藝術(shù)設(shè)計教育的搖籃”。
1983年,張仃正式從院長的位置上卸任。這位66歲的老人竟然高興地在地上打了個滾兒。終于自由了,終于可以專心開始自己的創(chuàng)作了!在接下來二十多年的歲月里,張仃的足跡幾乎遍布除了西藏、臺灣等地之外祖國所有的大好河山。他醉心于和自然的對話,每當打開冊頁,用筆描繪眼前的景色寫生,便忘掉了自己的存在,忘掉了周圍的一切。他把將焦墨這一中國山水畫中不為重視的小畫種發(fā)展為具有豐富表現(xiàn)力、可創(chuàng)作巨幅作品的大畫種,他通過線條的粗細、虛實、變形,畫面的節(jié)奏、韻律、空間,描摹出大自然的魂魄。莽莽蒼蒼,這紙上數(shù)以萬計的筆痕描繪的意象,其實正是這位世紀老人飽經(jīng)滄桑之后博大的胸懷與精深的哲思。雖然只有一種色彩,我們卻看到了春山如黛,雖然是焦墨枯筆,我們卻聽到了水流潺潺……
張仃,中國美術(shù)的驕傲。回顧張仃的百年,他從一名心懷家國的熱血青年,到投奔延安的革命文藝先鋒,從新中國的首席設(shè)計師到中國設(shè)計教育的奠基人,從裝飾繪畫風格的探索者到一代焦墨山水的藝術(shù)大家,他總是立于時代的潮頭浪尖;同時,他又是一名純粹的藝術(shù)家,他的藝術(shù)橫跨漫畫、建筑、設(shè)計、壁畫、中國畫多個類別,他無所不涉、無所不能,唯有藝術(shù)是他畢生的追求。
張仃,用他的一生,為我們?nèi)绾问刈o與傳承中華文脈,給予了永恒的典范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