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語(yǔ):
隨著這兩年的“抽象熱”,許多抽象藝術(shù)家愈加頻繁的走入我們的視野。2016 年初在今日美術(shù)館舉辦的“抽象藝術(shù)研究展”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十六位藝術(shù)家匯聚一堂,讓我們得以看到當(dāng)代中國(guó)抽象藝術(shù)家最高級(jí)別的集體亮相,譚平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譚平與其他抽象藝術(shù)家類(lèi)似,一方面早就不在乎作品的風(fēng)格、觀念等外在形式,而是在不斷回到更加自由,鮮明的個(gè)人化表達(dá);另一方面,因?yàn)樽髌返姆蔷呦笮院屠碚摲矫娴南鄬?duì)滯后,他姑且也一直在參與著與“抽象”有關(guān)的方方面面的工作。他在努力將這一幾十年來(lái)一直默默發(fā)展的藝術(shù)家群體和他們的作品帶入人們的視野,力圖證明他們的存在對(duì)于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完整性和成熟度的價(jià)值。
在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整體原創(chuàng)能力下滑的時(shí)候,以譚平為代表的中國(guó)抽象藝術(shù)家保持了自身在藝術(shù)本體上的創(chuàng)造性,并提供了一條可供人們繼續(xù)思考挖掘的新的道路與空間,抽象“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一、“抽象”的涵義隨著時(shí)間的演進(jìn)而變化
做學(xué)生的的時(shí)候,總是希望通過(guò)某一種風(fēng)格,某一種樣式把自己的個(gè)性表達(dá)出來(lái),比如印象派、表現(xiàn)主義、抽象藝術(shù)甚至更多不同的方式。后來(lái)突然發(fā)現(xiàn),各種藝術(shù)語(yǔ)言都是外在的形式,如果要表達(dá)內(nèi)心的真實(shí),可能用最簡(jiǎn)單的語(yǔ)言就可以把內(nèi)心感受表達(dá)出來(lái)。所以,近些年的主要工作是在做減法,把這些風(fēng)格與流派的影響逐漸去除掉,也無(wú)所謂抽象不抽象。這是在多年的藝術(shù)經(jīng)歷過(guò)程中慢慢體會(huì)到的。
上世紀(jì) 80 年代末到了柏林藝術(shù)大學(xué)學(xué)習(xí),對(duì)抽象藝術(shù)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認(rèn)識(shí)到今天的抽象藝術(shù)不僅僅是一個(gè)形式的問(wèn)題,它經(jīng)過(guò)了近一百年的發(fā)展,抽象概念的認(rèn)知已經(jīng)有很大的改變。今天你做的“抽象”只不過(guò)是沒(méi)有具體形象的,或者是無(wú)法識(shí)別的形象。事情的關(guān)鍵也不在是不是“抽象”的問(wèn)題。
今天看似抽象藝術(shù)的展覽很多,其內(nèi)涵已經(jīng)有多重詮釋。每個(gè)藝術(shù)家也都呈現(xiàn)不同的面貌。在這個(gè)領(lǐng)域,大家對(duì)于“抽象”這個(gè)詞的理解也是多元化的,今天的“抽象藝術(shù)”已經(jīng)不是一個(gè)藝術(shù)的風(fēng)格與流派,每個(gè)人都是一個(gè)獨(dú)立的個(gè)體,看起來(lái)很散,但這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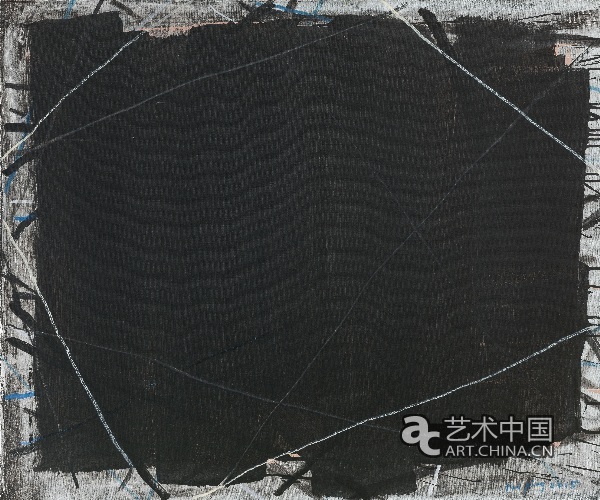
我覺(jué)得,現(xiàn)在特別需要做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好好研究抽象藝術(shù)家的個(gè)案。比如今日美術(shù)館“抽象藝術(shù)研究展”中的藝術(shù)家,每個(gè)都是一個(gè)很好的個(gè)案。他們成長(zhǎng)的過(guò)程都有相似之處,如大都經(jīng)過(guò)學(xué)院的美術(shù)教育。后來(lái)的道路就有了變化,一部分出國(guó),一部分在國(guó)內(nèi),有的是自由藝術(shù)家,有的在體制內(nèi),經(jīng)歷各有不同。從事抽象藝術(shù)的原因,以及對(duì)抽象的認(rèn)識(shí)也有很大區(qū)別。如果把這些個(gè)案做深入,找到他們共性特征的話(huà),那中國(guó)的抽象藝術(shù)也就誕生了。
另一方面,就是藝術(shù)批評(píng)界能夠從更高的層面觀察和研究一下這些從事抽象藝術(shù)三十多年的藝術(shù)家,直到今天還有不斷創(chuàng)新的勁頭,現(xiàn)在的作品看起來(lái)還是挺新鮮的。他們需要理論界和批評(píng)界給這些人一個(gè)很好的判斷和定位,如果簡(jiǎn)單的局限于“抽象”的范圍來(lái)概括的話(huà),是不夠的。應(yīng)該把他們放到中國(guó)美術(shù)史發(fā)展的框架之中,去看看他們的意義到底是什么。開(kāi)玩笑說(shuō),中國(guó)的抽象藝術(shù)是需要追認(rèn)的,如何放到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的框架之中,現(xiàn)在就要看理論界的高手了。

向羅斯克致敬_布-丙烯_120x120cm_2015
二、一件作品顯得不倫不類(lèi),不中不西,可能恰恰正是今天的現(xiàn)實(shí)和文化包容性的體現(xiàn)
中國(guó)的當(dāng)代藝術(shù)大多都是以西方的視角來(lái)看的,包括帶有中國(guó)符號(hào)和與意識(shí)形態(tài)有關(guān)的作品。而抽象藝術(shù)家的作品,表面看來(lái)沒(méi)有了可識(shí)別的符號(hào),也沒(méi)有了意識(shí)形態(tài)的特征,但它卻能真正以視覺(jué)的方式,呈現(xiàn)中國(guó)的文化特征。這種東西一旦被發(fā)現(xiàn)并闡述好的話(huà),它就能代表一個(gè)國(guó)家真正的文化精神,就像日本的“物派”和韓國(guó)的“單色繪畫(huà)”。
中國(guó)的藝術(shù)家對(duì)寫(xiě)實(shí)繪畫(huà)的鑒別經(jīng)驗(yàn)非常豐富,可以精確的分出不同寫(xiě)實(shí)藝術(shù)家細(xì)微的區(qū)別到底在哪,能看出在造型和色彩感覺(jué)上些微的不同。但是對(duì)于抽象繪畫(huà),卻沒(méi)有這樣的經(jīng)驗(yàn),在他們看來(lái)都是一樣的,或者只能大略分為冷抽象和熱抽象。如果這樣的話(huà),那根本就分不出“物派”和“極簡(jiǎn)主義”的區(qū)別了,更分不出相同風(fēng)格藝術(shù)家的不同了。
“中國(guó)抽象”我認(rèn)為是一個(gè)假問(wèn)題。每個(gè)藝術(shù)家都不可脫離它生長(zhǎng)的環(huán)境影響,更沒(méi)有一個(gè)絕對(duì)概念中的“中國(guó)”。有些作品表面上看起來(lái)“很中國(guó)” ,可能并不是真正的、今天的中國(guó)。與此相反,一張畫(huà)看起來(lái)“不中不西,不倫不類(lèi)”,但是它背后的東西有可能恰恰是當(dāng)代中國(guó)的。
在中國(guó),今天的每一個(gè)人,即學(xué)習(xí)中文,也學(xué)習(xí)英文,吃麥當(dāng)勞、穿耐克、開(kāi)奧迪,很多東西都是混雜的,可以說(shuō)沒(méi)有什么是純粹的。刻意把自己的作品弄得“很中國(guó)”,其實(shí)是一個(gè)假象,這本身正是西方式的思維,與東方的哲學(xué)觀是截然不同的。一個(gè)東西顯得不倫不類(lèi),不中不西,這是自然生長(zhǎng)的產(chǎn)物,可能恰恰正是今天的現(xiàn)實(shí)和文化包容性的體現(xiàn)。
三、表現(xiàn)方法的不斷變化,并沒(méi)有遮蔽“譚平”
很多抽象畫(huà)家都是從具象繪畫(huà)一點(diǎn)點(diǎn)發(fā)展到抽象繪畫(huà)的,我也不例外。都是擺脫了對(duì)具體物象的描述,尋求更為自由的表達(dá)方式。抽象藝術(shù)的本質(zhì)就是追求個(gè)人價(jià)值的充分體現(xiàn)。我的藝術(shù)都是隨著個(gè)人生活經(jīng)歷的變化而變化。作品中的顏色、線(xiàn)條的變化都是與我的經(jīng)歷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敏感是一個(gè)藝術(shù)家最重要的東西,生命中的任何一次變化都會(huì)影響到藝術(shù)家脆弱的神經(jīng)。我很希望通過(guò)瞬間的表達(dá),呈現(xiàn)生命的永恒。只有這樣,“你”永遠(yuǎn)活在你的每一件不同的作品之中。
因此,雖然我采用的繪畫(huà)方法不斷在變化,但最終大家看到的還是“譚平”,而不是很“中國(guó)”,或是“中國(guó)抽象”。自然長(zhǎng)出來(lái)的東西,才是最生動(dòng)和真實(shí)的。
四、“抽象熱”是表面現(xiàn)象
這幾年抽象藝術(shù)比較熱,一方面是因?yàn)槠渌乃囆g(shù)形式都弱化了,沒(méi)有新的流派來(lái)替代,所以抽象藝術(shù)就顯現(xiàn)出來(lái)了,抽象藝術(shù)一直存在,它頑強(qiáng)地生長(zhǎng)在主流之外。另一方面就是普通大眾的審美在不斷提高,看慣了具象繪畫(huà)覺(jué)得沒(méi)什么意思了,愿意有一個(gè)更加個(gè)人化的選擇。再就是市場(chǎng)表現(xiàn)越來(lái)越好。這幾個(gè)方面湊成所謂“抽象熱”。
抽象藝術(shù)的市場(chǎng)一直處于一個(gè)相對(duì)比較正常的狀態(tài)。所謂“抽象熱”對(duì)于抽象藝術(shù)家來(lái)說(shuō)影響不是很大,無(wú)論市場(chǎng)不好的時(shí)候,還是好的時(shí)候,也都是在做自己的事,市場(chǎng)影響不了我。可能市場(chǎng)對(duì)年輕人影響大一些,有時(shí)市場(chǎng)會(huì)決定他們是否繼續(xù)進(jìn)行抽象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

展覽現(xiàn)場(chǎng)
五、關(guān)于 2015
2015 年,我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xué)美術(shù)館做了“彳亍”的展覽,我把二十多件紙上作品鋪在臺(tái)子上,放置在空間里,還有一個(gè)錄像作品。當(dāng)時(shí)有五個(gè)展覽同時(shí)開(kāi)幕,很多觀眾非常喜歡我的這個(gè)展覽,覺(jué)得很有意思。觀眾俯視或是蹲下來(lái)看這些作品,是在閱讀。
這個(gè)展覽之前在北京的偏鋒藝術(shù)空間也做過(guò),但我覺(jué)得這個(gè)展覽拿到美國(guó)之后反映比國(guó)內(nèi)還要強(qiáng)烈。因?yàn)槿绾斡^看的問(wèn)題在國(guó)內(nèi)沒(méi)有對(duì)比,大家也不太在乎怎么觀看的問(wèn)題,但當(dāng)拿到另一個(gè)文化背景的空間中去時(shí),他們會(huì)突然發(fā)現(xiàn)東方人的觀看方式與他們真的不一樣。
第二個(gè)展覽就是在今格藝術(shù)空間的個(gè)展,更多是關(guān)注空間、作品與色彩之間的關(guān)系。每張作品的墻面顏色都不一樣。

歷史 History 300cm×400cm 布面丙烯 2015
五月我在中國(guó)美術(shù)館做了與瑞士藝術(shù)家卡斯特利的對(duì)話(huà)展。這個(gè)展覽還將在2016 年五月份在上海舉辦,這次展出的作品基本上將會(huì)是合作完成的,他畫(huà)一半,我來(lái)畫(huà)另一半。會(huì)有很多不可預(yù)知的效果發(fā)生。
2015年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在今日美術(shù)館舉辦的“抽象藝術(shù)研究展”。這個(gè)展覽算是對(duì)中國(guó)抽象藝術(shù)年的一個(gè)小小的總結(jié),希望從此開(kāi)始,一步步深入的對(duì)中國(guó)抽象藝術(shù)進(jìn)行研究。下一步怎么做?很多人也在關(guān)注。包括我們做的研討會(huì),很多人也在積極的參與,都覺(jué)得有必要好好討論一下。一方面希望策劃年輕的抽象藝術(shù)家的展覽以及多媒介的抽象作品中。另外也希望把這個(gè)展覽帶到國(guó)外的美術(shù)館去展覽,同樣的東西放到不同的環(huán)境和視角之下,會(huì)有完全不同的評(píng)價(jià)。
兒時(shí)的胡涂亂抹已經(jīng)沒(méi)有了記憶。我猜想,那時(shí)候一定是沒(méi)有什么目的,只是囿于本能。后來(lái)去了小學(xué),上了中學(xué),我就在作業(yè)本和書(shū)的空白處畫(huà)畫(huà)兒,畫(huà)我想象中的人和物。
十三歲,我開(kāi)始拜師,正式學(xué)習(xí)素描。從此“寫(xiě)生”這個(gè)詞,替代了“畫(huà)畫(huà)兒”。
寫(xiě)生的裝備要有畫(huà)板和畫(huà)架,還要把畫(huà)板放在畫(huà)架上立起來(lái)畫(huà)。瞇著眼觀看遠(yuǎn)處桌面上的立方體,用削尖的鉛筆,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描繪,真實(shí)地把我看到的東西畫(huà)到紙上。通過(guò)寫(xiě)生我發(fā)現(xiàn)了,以往物體看不到的結(jié)構(gòu)、透視、光影,還有塑造物體的繪畫(huà)方法,“寫(xiě)生”中有太多的驚喜,使我完全迷戀在再現(xiàn)的狀態(tài)中。
后來(lái),我上了中央美院。在寫(xiě)生的對(duì)象變得更為復(fù)雜的同時(shí),還添加了新課題“創(chuàng)作”。為了“創(chuàng)作”,我好比一個(gè)無(wú)頭的蒼蠅,到處亂飛。一會(huì)兒學(xué)某大師的風(fēng)格,一會(huì)兒又被某同學(xué)的方法所吸引。回望那個(gè)時(shí)候的作品多多少少都透出些學(xué)習(xí)大師的痕跡與受到不同流派的影響。然而,也正是經(jīng)歷了這個(gè)時(shí)期,我的“創(chuàng)作”與“習(xí)作”不再分家,統(tǒng)稱(chēng)“作品”。
在德國(guó)學(xué)習(xí)的五年,自己面對(duì)的并不僅僅是學(xué)院的藝術(shù)課程和博物館大師的作品。真正影響我的是在那里學(xué)習(xí)與生活的全部:與你打交道的人,社會(huì)環(huán)境,看問(wèn)題的多元視角,價(jià)值觀、生活觀乃至世界觀。事實(shí)上,我們?cè)?jīng)熟悉的經(jīng)典作品,一旦真實(shí)地出現(xiàn)在自己生活的場(chǎng)域中,它對(duì)我的震撼遠(yuǎn)沒(méi)有想象中的強(qiáng)烈。在那里,慢慢的,我開(kāi)始真正理解這些大藝術(shù)家及其作品產(chǎn)生的淵源。
靜,能令人思考。遠(yuǎn)離中國(guó),可以自覺(jué)地開(kāi)始內(nèi)醒。我是誰(shuí)?從哪里來(lái)?要到哪里去?思考的過(guò)程與表達(dá)的需要,開(kāi)始對(duì)抽象繪畫(huà)的研究與實(shí)踐也就變得自然而然了。
1994 年春,學(xué)成歸來(lái),我重返美院做教師,并開(kāi)始籌建設(shè)計(jì)專(zhuān)業(yè),后來(lái)又從事教學(xué)管理工作,俗稱(chēng)“雙肩挑”。學(xué)院規(guī)模變大,日常事務(wù)也變得越來(lái)越龐雜,除了正常教學(xué),我的業(yè)余時(shí)間也幾乎全部被學(xué)院事務(wù)所占滿(mǎn),全然是一種超負(fù)荷的工作狀態(tài)。我的角色,也由一個(gè)專(zhuān)業(yè)畫(huà)家轉(zhuǎn)變成一個(gè)教育管理者。基于對(duì)教學(xué)的不舍,我在痛苦與糾結(jié)中逐漸適應(yīng)了這個(gè)角色,心平氣和地在做一個(gè)“業(yè)余畫(huà)家”。業(yè)余畫(huà)家不太求結(jié)果,更在乎如何在有限的業(yè)余時(shí)間里去感受畫(huà)畫(huà)的快樂(lè),在沉靜中去尋回曾經(jīng)的初心。正是對(duì)“業(yè)余時(shí)間”的有效運(yùn)用,形成了我自己的創(chuàng)作方法。
擠出空閑時(shí)間來(lái)到工作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畫(huà)面涂抹一遍。這種涂繪是在主觀限定的時(shí)間內(nèi)完成,只有改變以往畫(huà)畫(huà)的常態(tài),不斷與過(guò)去的習(xí)慣相對(duì)抗,才有可能在限定的時(shí)間內(nèi)完成一個(gè)最基本的工作:“涂滿(mǎn)畫(huà)面”。“涂滿(mǎn)畫(huà)面”的行為,消解了對(duì)繪畫(huà)結(jié)果的述求,使“體驗(yàn)過(guò)程”成為我畫(huà)畫(huà)的核心議題。一張 2 乘 3 米大的畫(huà)布用 10 分鐘像油漆匠似的涂抹一遍,已然是一個(gè)不輕的體力活。然而我卻非常享受為“涂滿(mǎn)畫(huà)面”而去不斷“覆蓋”已經(jīng)存在的作品這個(gè)過(guò)程抑或行為,因?yàn)檫@里指涉的是一種態(tài)度和勇氣。
可以說(shuō),我的作品時(shí)刻都處于未完成和重新開(kāi)始的狀態(tài)。無(wú)論畫(huà)面看起來(lái)如何的完美,都存在被“覆蓋”的可能。覆蓋一幅并不完滿(mǎn)的畫(huà),通常都不會(huì)太在意,若是要去覆蓋一幅幾近完美的畫(huà)作,內(nèi)心就會(huì)有糾結(jié)與不舍,和難以名狀的痛。覆蓋過(guò)去——如同否定自我,需要勇氣。它既是一個(gè)決絕的行動(dòng),更是一次“再生機(jī)緣”的創(chuàng)造。
覆蓋的行為,會(huì)改變常態(tài)的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與哲思觀念,刺激麻木的思想與靈魂。越是完美的畫(huà)面被“覆蓋”,這個(gè)行動(dòng)越能體現(xiàn)其意義。
“覆蓋”這個(gè)行為,從物質(zhì)層面來(lái)看,圖像雖被覆蓋,它曾經(jīng)的樣貌仍然存在于層層顏色之下,如同人類(lèi)的歷史,經(jīng)過(guò)了多次自然破壞和人為摧毀,我們依舊可以看到和感受到時(shí)代的痕跡與氣息。“覆蓋”是時(shí)間切片的疊加。從精神層面來(lái)看,“覆蓋”這個(gè)行為,如同修行,強(qiáng)心健智。
我很少回顧自己的藝術(shù)歷程,自覺(jué)還沒(méi)到回憶的時(shí)節(jié)。然而,為了籌備“畫(huà)畫(huà)”這個(gè)展覽,我把從十幾歲到新近的畫(huà)作,一一擺放開(kāi)來(lái)做了梳理,并挑選出展覽的作品。面對(duì)這些相隔四十余年的畫(huà)作,從“畫(huà)它”、“畫(huà)我”到“我畫(huà)”這一漫長(zhǎng)過(guò)程的轉(zhuǎn)變,我恍然明了,走過(guò)這么多年,畫(huà)中的我并沒(méi)有改變,我還是那個(gè)愛(ài)“畫(huà)畫(huà)”的我。可以說(shuō),“畫(huà)畫(huà)”是我的常態(tài),從兒時(shí)到今天,一直是拿著一支筆在畫(huà)畫(huà)。“畫(huà)畫(huà)”,并不需要體現(xiàn)一個(gè)人的身份,也無(wú)關(guān)乎年齡長(zhǎng)幼,它只是出于本能的需要。
“畫(huà)畫(huà)”是我這次展覽的名字,它可以非常準(zhǔn)確傳達(dá)我對(duì)藝術(sh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