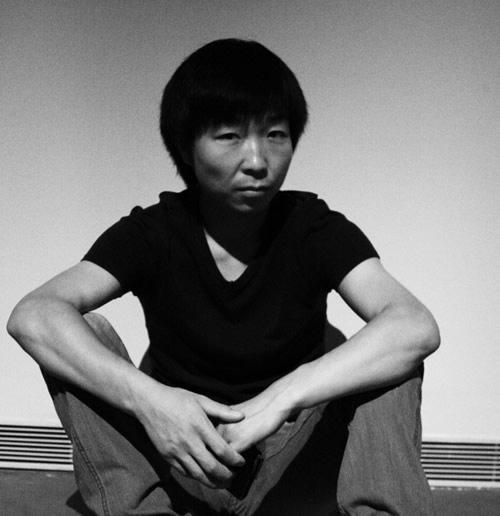 像所有油畫系的學(xué)生一樣,閆冰在四年學(xué)習(xí)過程中嘗試著不同的繪畫風(fēng)格,直到畢業(yè)創(chuàng)作逼近。雖然他還沒有很明朗的看到繪畫之外的其他可能性,但他分明厭倦了畫布上的形式游戲(也可以說是對(duì)油畫語(yǔ)言的探索),他需要一次冒險(xiǎn),哪怕是以失敗告終,也不愿給自己的大學(xué)畫上一個(gè)平庸的句號(hào)。2007年的畢業(yè)展上他展出的作品是在保留了動(dòng)物外形的整張皮毛上描繪動(dòng)物的本體形象,這組取名為“生死疲勞”的作品在美院畢業(yè)展上顯得陌生而神秘,皮毛上的動(dòng)物形象用線條簡(jiǎn)單勾勒,有著人類原始造型的色彩與張力,生命的尊嚴(yán)與苦難被表達(dá)的直接而強(qiáng)烈,與美院繪畫教學(xué)里的形象塑造相去甚遠(yuǎn)。由于初次使用皮毛這種媒介,對(duì)材料的特性把握不到位,作品沒有達(dá)到他預(yù)想中的效果,但這次嘗試給他日后的創(chuàng)作開啟了一扇門。 畢業(yè)后的兩年多里,閆冰在深入研究皮毛的材料特性的同時(shí)對(duì)泥土,承載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記憶、味道、和情感的泥土,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這些泥土與有著平凡生活之溫度的物件——火爐,長(zhǎng)凳,木床,木柜,床墊等等達(dá)成了耐人尋味的形式結(jié)合,有附著,生長(zhǎng),流淌,包裹,有更為艱苦與純粹的:他用泥土一點(diǎn)一滴積累起來的超越時(shí)空歸屬感的形體,這些形體猶如燕子銜泥般被累積的過程對(duì)藝術(shù)家來說是一個(gè)苦行僧式的修行過程。與此同時(shí)閆冰用皮毛做的作品也脫離了畢業(yè)創(chuàng)作時(shí)的直白與強(qiáng)烈,更為含蓄,雋永。在這些作品中,閆冰一直扮演著一個(gè)“講故事者”的角色,把平凡瑣碎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娓娓道來,雖然沒有所謂高級(jí)文化的狡黠智慧或廢黜嚴(yán)肅性的反諷幽默,故事仍然動(dòng)聽且吸引人,這是因?yàn)樗臄⑹龊褪闱橛猩詈竦那楦泻透兄姆e淀基礎(chǔ),充滿了生命的氣息。這種氣息在一件名為《他》的作品里顯得尤其強(qiáng)烈,一個(gè)竹編的背簍,綴滿了長(zhǎng)長(zhǎng)的麻絲,這個(gè)背簍已經(jīng)脫離了它的實(shí)用功能而成為一個(gè)生命個(gè)體,或是群體生命的隱喻,麻絲的質(zhì)感與形態(tài)似乎暗示著這個(gè)背簍已經(jīng)孤寂千年,而生命的氣息仍綿延不絕。 由于作品的材料和形式與中國(guó)鄉(xiāng)土生活的密切聯(lián)系,閆冰的作品很容易被人誤解為“鄉(xiāng)土情懷”的產(chǎn)物,事實(shí)并非如此簡(jiǎn)單。中國(guó)當(dāng)代社會(huì)語(yǔ)境的復(fù)雜性與開放性強(qiáng)烈吸引著藝術(shù)家們對(duì)于宏大問題與外來理論系統(tǒng)的關(guān)注。藝術(shù)家們或從各個(gè)角度討論社會(huì)、歷史的發(fā)展與進(jìn)步(尤以“持不同政見者”身份來討論發(fā)展與進(jìn)步者為眾),或?qū)⒆髌穭?chuàng)作指向文本系統(tǒng),尋求高深理論系統(tǒng)里的支點(diǎn)或意義。以閆冰的生活成長(zhǎng)經(jīng)歷來觀察世界,一切都是從泥土中生長(zhǎng)出來,最終回歸到泥土之中,那些轟轟烈烈的事件與人物除了冷冰冰的紀(jì)念碑似乎沒有給他們賴以生長(zhǎng)并最終埋葬他們的土地留下值得撫摸與回味的痕跡。相對(duì)于此,閆冰選擇的是一個(gè)內(nèi)向的、觀照自我與生命內(nèi)在歷程的創(chuàng)作方向,生命的載體在他的作品里不僅是動(dòng)植物與人,也是承載了生命的溫度與痕跡的物件,他對(duì)這些溫度與痕跡加以個(gè)人化的保留與詮釋,去發(fā)現(xiàn)什么是可以享受的,什么是可以挽回的。這些作品就像角落里的光,照亮的首先是藝術(shù)家自己,能否照亮其他人,取決于他們是否與藝術(shù)家一樣,以同樣質(zhì)樸的方式面對(duì)生命與生活,因?yàn)檫@些作品沒有一個(gè)道德性批判立場(chǎng)去指引或暗示觀眾,對(duì)于“標(biāo)準(zhǔn)”已然崩潰的現(xiàn)代人來說,這是痛苦不堪的,精神赤貧的人們無法再承受自己對(duì)于物質(zhì)是同樣的無知這一事實(shí)。 |